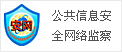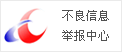中国的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导致其债务风险是发散的、积累的与不可控的,中央政府成为最后的兜底者,地方官员不需要为借债行为承担责任,借债扩张投资的冲动难以遏制,传统经济与财政发展模式则难以改变。不过,在增加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规范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特别是明确地方政府的征税和发债权力的基础上,中国也是可以出现地方政府破产的——没有什么制度比破产对地方政府的肆无忌惮地举债更具威慑力量,因此,需要逐步探索建立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地方政府破产制度。
刘立峰
最近,曾经是全美第五大城市、“汽车之城”底特律向州法院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自1937年以来,美国有约600个城市申请破产。自金融危机爆发到2011年,约有15个城市申请破产。2012年,美国加州斯托克顿市等三座城市也相继宣布破产。美国的地方政府能够破产,那么中国的地方政府能否破产呢?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除了国防、外交等职能归属中央政府外,中央、州和地方政府各有各的法律、各管各的事、各征各的税、各发各的债。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能否破产是其内部的事情,与中央政府没有太大的关联,中央政府也没有义务为其债务兜底。中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权的严格控制下行使职权,由中央委派官员或由地方选出的官员代表中央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税收和发债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省以下政府没有税收的立法权,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既然地方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也就不可能要求地方政府为其债务负责;既然地方政府预算不能列赤字、不能发行债券,也就不承认地方政府真正拥有债务,地方政府也就无所谓破产之说。
企业破产意味着企业清盘与不复存在,而美国地方政府破产只是财政的破产,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政府破产重在通过财政平衡、债务重组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而不是让政府消失。但尽管如此,政府破产对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地方政府破产具有风险隔离作用,由于地方政府可以申请破产,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是隔离的,一个城市的问题不会带来整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破产还具有止损作用,可以把债权人的损失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地方政府破产也具有惩戒作用,破产城市的公共支出将大幅缩减,百姓要承担更高的税负,对破产负有责任的官员,其仕途将受到影响;地方政府破产更具有警示作用,提醒人们反思地方经济和财政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并及时转变发展方式。相比之下,中国的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导致其债务风险是发散的、积累的与不可控的,中央政府成为最后的兜底者,地方官员不需要为借债行为承担责任,借债扩张投资的冲动难以遏制,传统经济与财政发展模式则难以改变。
地方政府无破产之忧,一旦下级政府出现债务危机情况,中央政府势必要出手相救,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的是全体纳税人的利益,虽然掩盖了一时的风险,却可能累积成全国性的系统危机。1999年,国家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1999—2000年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先后收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这些不良资产的产生有些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有些借款主体本身就是政府下属部门和企业,剥离的不良资产实质上就是无法清偿的地方政府债务。资产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财政部核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包括划转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部分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实际上是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出资、发债以及隐性货币化方式对债务进行了处置,风险最终承担者是全体国民。
近期,随着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以及还债高峰到来,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出现上升的趋势,为此,2012年2月,财政部联合银监会下发《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规定各省级政府可设立或授权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参与辖区内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工作,并严格要求采取债务重组方式,不得对外转让。在银行不良资产反弹的压力下,允许省级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辖区内不良资产,实际上在告诫地方:盲目投资需自担责任,中央政府不再全盘揽责,旨在缓解以往剥离不良资产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但是,首先,省级政府既无独立的发债权,又没有不良资产隐性货币化通道,实际上缺乏化解不良资产的能力;其次,更多的债务是由市、县两级政府造成的,由省级政府全盘负责债务处置,仍然无法解决市、县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再次,此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仅反映在银行不良资产方面,同时反映在地方债、城投债等债券市场上,以及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银行表外业务上,由此产生的风险可能对债券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仅仅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提出预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0.7万亿元,我们以审计署公布的部分城市债务余额两年增长12.9%计算,2011—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达到11.3万亿元、12万亿元。如果按照8%的利率计算,2010—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利息分别为0.86万亿元、0.9万亿元和0.96万亿元。而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净收益达到峰值的1.57万亿元,之后,2011年下降到0.95万亿元,2012年再下降到0.58万亿元。2010—2011年,土地净收益支付利息没有问题,而到2012年,土地净收益只能支付利息额的60%。由于土地收益是地方政府主要的还本付息来源,土地净收益与还本付息额的差距不断拉大,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清偿能力趋于下降。结合国家审计署的资料,2012年底,有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亿元,未来地方政府到期无法还债的情况可能频繁出现。
根据国际经验,判定是否破产的标准不是资不抵债,而是是否能够偿还到期债务。在德国破产法中,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一般的破产原因。法国破产法以“不能清偿”为破产的标准,而不是以“资不抵债”。日本破产法规定,法人不能以其财产清偿其债务时,可对其宣告破产。这表明即使法人的资产总额大于负债总额,只要其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即可破产。可见,当前,中国的某些市县政府确实已经达到破产的界限。应该说,除了《美国破产法》在第九章规定了“市政府债务的调整”,其他国家并没有将地方政府破产写入破产法。但是,有关地方政府破产的案例仍然在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单一制国家发生过,只是这些国家不是以破产的名义对地方政府进行处置。在日本,负债过高的市长宣布放弃自力更生再建财政的计划,经过一系列程序,该市就将被置于国家严格管理之下,成为“财政再建团体”,简单地说就是城市破产。可见,单一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地方政府不能破产的借口或障碍。在增加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规范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特别是明确地方政府的征税和发债权力的基础上,中国也是可以出现地方政府破产的。
没有什么制度比破产对地方政府的肆无忌惮地举债更具威慑力量。尽管破产并不会对地方政府职能产生影响,政府机构仍然在运作,但是,却要裁员、降薪,消减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开支,拍卖公共资产,实现收支均衡和财政的正常化。这一过程具有积极的惩戒和警示作用,是一种债务风险控制的长效机制。我们不希望中国出现底特律,但是,要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和扩散的局面,恰恰需要中国出现底特律。尽管美国曾经发生过几百个城市的破产保护问题,但是,相对于其几万个城镇以及上百年的城市发展历史来讲,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相反,这是用一个个城市危机化解替代了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发生。我们的城镇仍然非常年轻,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更需要一种长效的分散风险的机制,避免全体公民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重复买单。
需要逐步探索建立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地方政府破产制度。首先,我国的破产法并不包括企业之外的债务人,因此,可先按现有破产法的程序处理,将市、县、镇等地方政府,以及提供公益设施的公共派出机构纳入申请破产保护范围,并推动破产法的修改完善;其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政府的信用背书。中央政府必须向全社会做出不完全救助的表态,防止无条件救助产生的道德风险。应由省级政府负责市县政府的债务重组,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的预算要由省级政府监管。同时,中央政府有条件地给予转移支付,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原有债务,并在之后的政府预算中扣减;再次,应尽量简化破产程序,要在有利于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危机的同时,兼顾到大多数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要保证地方政府基本行政职能的运作。破产后果由地方政府与债权人共同承担;最后,要完善政府破产的制度环境。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法律体系。修改《预算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同时,制定《地方政府债务法》,规范地方政府负债的范围、审核权限、资金投向、偿债责任、危机处理等。